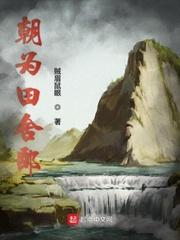第7小说>至尊灵妃:帝君太会撩 > 第八十一章 国丧(第1页)
第八十一章 国丧(第1页)
()凛冬之夜,天气本就寒冷刺骨,再加上近日天气持续恶劣,实在是入心冰凉。蓝泽筠二人在门口站了许久。身体已然忍受不住,打起颤来,百青皱了皱眉头,心里的热火全被浇灭,有些躁动的问蓝泽筠:“你说,都这么久了,这人还不来,是不是上官晨根本不想见咱?就算不想见也出来吭个声儿啊,这么冷的天儿,他再不来我就要冻成一块儿冰了。”
蓝泽筠如今的身体本就比常人弱的多,此刻只觉得寒风刺骨,四肢冰寒,就连血液也有些凝固的意味。
好不容易,终于有了脚步声,百青跳了跳脚,眼睛重新亮了起来。门闩再次响动,这回不是开了一条小缝儿,而是敞开了半张铁门。那人恭敬的将二人迎了进去,一路引到承德宫一处温暖的偏殿内。
屋里燃着散着淡淡幽香的银丝雪碳,很是暖和,百青自打进入偏殿就不大安分,两只灵动的狐狸眼来回瞟动,一会儿打量打量这个,一会儿伸手摸了摸那个,嘴里连连惊叹,喜欢的紧。
不出一刻钟,屋外有齿轮转动声响起,有宫人推门而入,恭敬的站在一旁,而后一道雪白色身影逐渐显露出来。
上官晨披着银白色的厚重皮草斗篷,面上毫无血色,看着很是憔悴,本来精致温润的五官如今全是疲劳之色。
百青自从那人进来便安分了许多,直立在蓝泽筠面前,直勾勾的盯着上官晨看。
上官晨进门看到二人,很是疑惑,不过心中一转,稍作打量,便知他二人绝非是曹公的人。于是出声问道:“你二人……可是找我?”
蓝泽筠闻言,浑身紧张,双手紧紧攥着斗篷不知道该如何开口。百青见状,轻轻撞了一下蓝泽筠,忽而假笑道:“哦…大皇子!久闻大名,我身边儿这位可是您多年前的挚友啊,您不记得了?不记得也没事,您日日繁忙,这些小事也着实没理由记得,此次我俩就是来拜访你的。”
百青热络的说着,上官晨偏头看了两眼蓝泽筠,努力搜寻着记忆,最后还是没有一点儿印象,心想二人半夜入宫,而且还不知从哪里找的曹公的牌子,着实匪夷所思。
虽然心里如此思索,不过上官晨面上看起来依旧和睦,嘴角轻轻一笑道:“二位我实在没见过,深夜进宫前来拜访,二位…也真是无人不同啊。”
百青尴尬一笑,瞬间有些不知所措,随即瞟了一眼蓝泽筠,心里暗骂到:我真以为你和人家是什么深交,如今来此,人家压根儿不认得你,惨了惨了,这下被你害惨了!
“我是清的挚友,今日来此,只为她。”
蓝泽筠一字一句,声音有些颤抖,但还算清晰的说了出来。上官晨立刻瞳孔放大,有些五味杂陈的看着蓝泽筠。
承德宫略微有些杂乱的书房,像是好久都没有人气,有些清寒,明亮的夜明珠下,一张乌木桌案上乱七八糟的放置着好几本杂记闲谈,桌面正中央放置着一张咏花图,四周都用玉质的镇尺规整的压着,上边儿的开的正茂盛繁华的牡丹芍药都没有丝毫色彩,只有一旁几朵含苞的玫瑰被精致的描了朱砂
红,一眼望去,极其扎眼娇艳。
上官晨轻轻抚了一下宣纸边缘,看着面前的人,有些颤抖道:“你是蓝泽筠?”
蓝泽筠闻言,将斗篷轻轻一提,直直的跪了下去,大理石地板上发出砰的一声巨响。
“是,是我…对不起她。”
上官晨闻言,轻轻闭上了眼睛,一双温润灵气的眸子,在这些年的浮浮沉沉中早就失了原有的光辉,两行清泪顺着眼角流了下来,畅通无阻的溜到下颚处,而后慢慢凝结,掉落了一颗透亮的水珠子。
足足有三刻钟,书房内悄然无声,上官晨正眼瞧着蓝泽筠,她又能好到哪里去呢,看样子,双目已然失了光彩,整个人瘦的厉害,面庞有些凹陷,双目亦是通红,不过跪的端正,直挺,看着一副病态。她心里也是不好受吧,修门之事,前前后后,他也是知晓全了。算是清儿为她舍身赴死,却终归不是她本意。
要说不恨蓝泽筠是不可能的,不过一年的深思中,恨意早就慢慢淡去,今日见了,倒觉得有些同病相怜。
上官晨长叹一口气道:“清儿从来没有对我提起过谁,除了你,你是第一个也是唯一一个,想来你在她心中应当是很重要的存在。”
上官晨每说一句,蓝泽筠的心就更痛一分。每次想到那张眼角带笑的脸庞,她都觉得无法呼吸。生离死别,皆是七情之苦,六欲负累。
“她在我心中亦是惟一,我答应过她,离了人世,稍后再会。”
上官晨摇了摇头道:“如今你的命亦是她的命,应当加倍珍稀才是,倘若她舍身救你,你有命活着,却如此糟蹋,那清儿岂不是白白牺牲。我断然不允许。”
蓝泽筠愣了愣,问道:“你不怪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