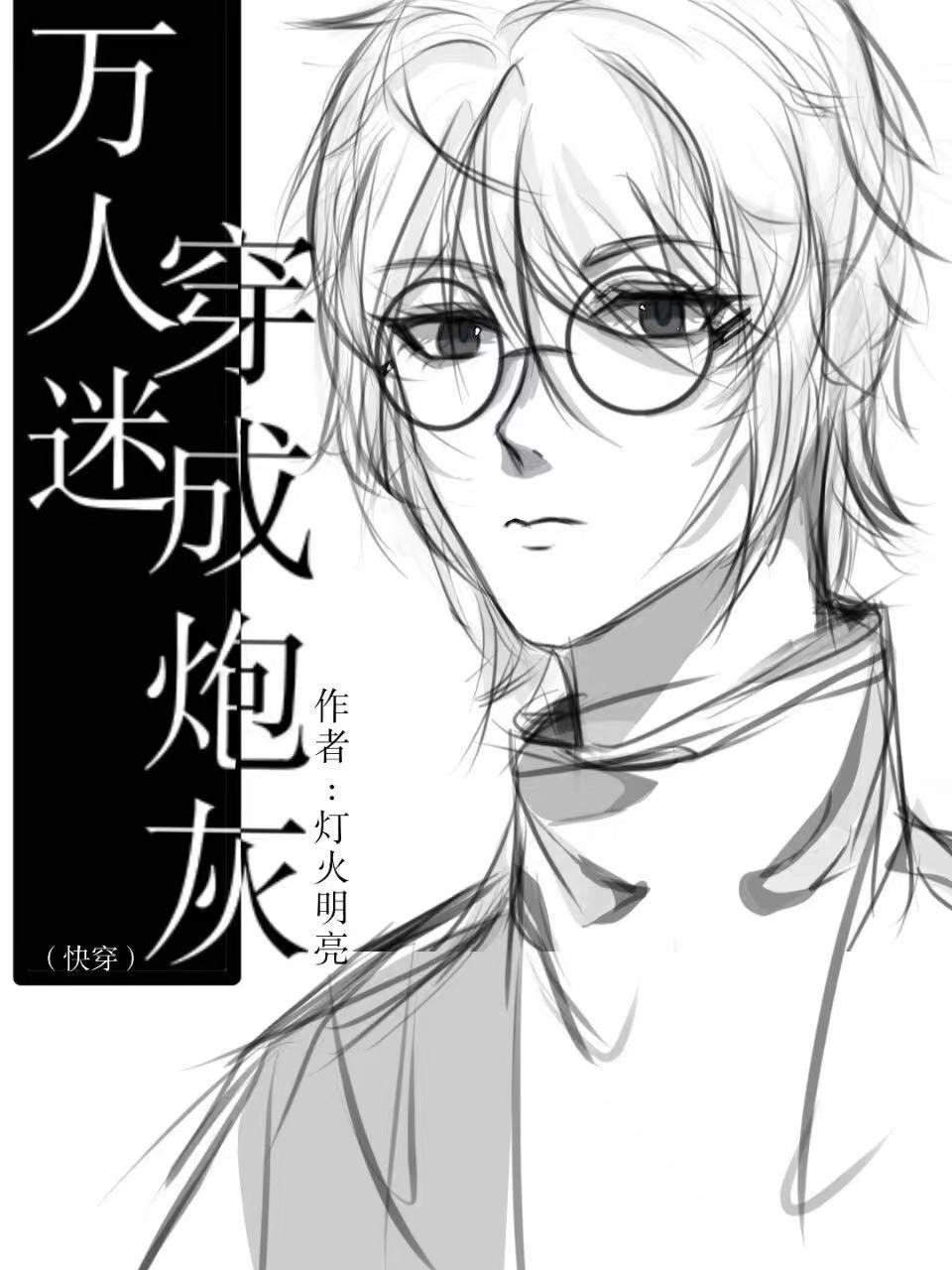第7小说>玉脂记 > 第10章(第2页)
第10章(第2页)
“有伤到哪里吗?”说完补充,“我才想起来问。”
赵绥绥道:“头皮被抓破了,不过应该不严重。”
“给我看看。”沈溟沐走过来,紧挨着赵绥绥坐下。赵绥绥主动把头凑过去,沈溟沐拨开她的发丛,找到伤口,“不算严重,但也不能掉以轻心,一会儿回到营地涂些药膏。”
“我们什么时候能回去?”
“衣服烤干了就回。”看看天上日头,“这个时辰纵算走着回去天黑前也能走到营地。”
赵绥绥吁一口气,还好不用单独和他过夜,不然……不然……她抱紧自己。
“绥绥。”他忽然叫她,“饿了吗?”
“饿……有、有点饿……”他唤她名字时的语气好温柔。
“但是干粮不是在马身上麽……”
“我看溪里颇有几条肥鱼,我叉来给你吃。”
木棍削尖尖,衣摆扎在腰间,卷起裤脚,光足涉水。
赵绥绥好奇沈溟沐怎样叉鱼,跟过去瞧,溪水中尽是碎石块,瞧的她好不揪心:“沈大人小心,勿割伤了脚。”
沈溟沐手指竖在唇上,示意她噤声。双目紧盯溪流,手捏着鱼叉,全神贯注。鱼儿意识不到近在眼前的危险,摆尾游来,沈溟沐瞅准肥大的一条,猛地一叉!
赵绥绥心提到嗓子眼,等不及地问,“叉到了吗?叉到了吗?”
看着鱼叉提起,上串着一条活蹦乱跳的大鱼,兴奋拍手:“沈大人好厉害!”
“叉条鱼而已,算什么厉害。”他上岸,屈指弹她,水星儿蹦到脸上,腥腥凉凉。
鱼儿开膛破肚,拽几片带香气的叶子揉成汁里外涂抹上,使刀划出道子,虽未放盐,胜在新鲜,不出两刻钟,焦香味飘溢入鼻。
沈溟沐割下一片鱼尾巴用藿香叶子包好递给赵绥绥。热气熏染下,藿香的气味浓郁异常。赵绥绥咬下一小块,外皮焦焦,雪白的鱼肉嫩嫩。
“没放盐巴,滋味怕是不够鲜美,权且充充饥。”
鱼肉烫牙,赵绥绥勤倒换,半晌才顾上回沈溟沐的话:“没有,蛮好吃。”
又问:“沈大人怎么会做叉鱼烤鱼这种事?”
“不像是我这种身份的人会做的?”
“是啊,这些都是下人们做的事。”赵绥绥心直口快说完,惊觉这话太无礼,胳膊伸到衣里,悄悄拧自己。
沈溟沐倒是坦然:“少年时我有过一段浪迹街头的经历,无人供我饱饭,无人供我衣穿,遂自学了一身填饱肚子的本领,叉鱼只是其中微不足道的一项。”
“诶?”赵绥绥惊讶。心里浮起一堆疑问,没等问出口,沈溟沐又往她手里塞了一块烤鱼,“快吃吧,吃完了咱们好上路。”
赵绥绥怀着复杂的心情吃完。衣服早给火烘干了,赵绥绥换上,将沈溟沐的衣服还给他。
沈溟沐套上衣服,忽地鼻翼微动,笑道:“每次被你穿过的衣服都香喷喷的。”
赵绥绥这次再不能推到熏衣上去,讷讷道:“想必是澡豆留香持久之故。”
两人沿着来时的路往回走,走着走着竟然看到跑掉的两匹马站在路边吃草,大喜,骑上去驰回营地。
营地里除去几个生火做饭的粗婢小厮再无闲人,朱樱和商子煜还没回来,班雀季鸿更别提了。
“小狐锦豹儿竟也不在,还想叫她们给我梳头呢。”赵绥绥的头发先前被猴子抓散,一直未束。
沈溟沐打帐篷里取来一盒药膏,把赵绥绥按在交椅上,“勿动,我给你涂药。”
其时明月初升,遥挂枝头,清辉遍洒下来,亮堂堂,不需灯烛亦自分明。
赵绥绥感受着头皮间的清凉意,如嚼薄荷。沈溟沐涂完药膏,撩起一捧头发,与她简单绾了个螺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