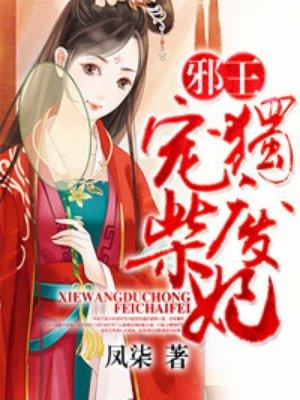第7小说>阴郁受心死后重生了 > 第114章(第1页)
第114章(第1页)
堂堂礼部侍郎大人,竟然挪用已故妻子的嫁妆,说出去岂不是让人笑
容钰在前院儿发作一通,只觉得神清气爽,这段时间以来的憋闷与压抑都减轻不少。
回到碧影榭他就让墨书收拾东西,准备去京郊的庄子里住一段时间。这容府让他住的实在难受,干脆出去透透气。
这时前院儿发生的事已经传遍容府了,秦嬷嬷知道后有些担忧,“哥儿,你不会真要和老爷断绝关系吧?”
墨书在一旁嘀嘀咕咕,“断绝了好,省的哥儿老是跟他们生气。”
秦嬷嬷掐了他一下,“休得胡说。”
秦嬷嬷又道:“哥儿,父子血缘不可断,虽说老爷着实偏心了些,可礼部侍郎嫡子的身份却可以庇护您在京都安稳行事。容老奴说一句不好听的,这万一真断了,日后恐有麻烦上门,后患无穷。”
秦嬷嬷说得委婉,实则就是容钰从前行事乖张,招惹了不少人,多亏容修永的地位保住了他,若是真断绝了关系,那些跟他有过节的人,看他不顺眼的人,恐怕都得上来踩一脚。
容钰浑不在意地把玩着一只玉珠子,“父亲想跟我断,我又能有什么法子。”
如果容修永真要和他断绝关系,他还乐得轻松。在这等级森严的古代,压在人们头上的除了皇权便是父权。倘若没了父权礼法的压制,从此天高海阔,他一身自由。
至于秦嬷嬷担心的那些“麻烦”——若是落井下石的流言蜚语,那对他来说不痛不痒。若是真欺负到他头上,他会让那些人见识见识现代科技力量。
容钰把手里的珠子扔起来又接住,只觉得心情一片大好,按捺不住想找人说说话。
“嬷嬷,母亲留下的嫁妆可都我这里?”
秦嬷嬷收拾行李的手一顿,犹豫回答道:“不全在,有一些在老爷那里。”
容钰:“嗯?”
秦嬷嬷找来账本,仔细翻了一翻,递到容钰面前,“哥儿,你看,有一间首饰铺子,一间米铺,一间成衣铺,还有京郊的一百亩水田、两百亩旱田,这些都是老爷把持着,每年的进项都入了府中中馈。”
见容钰面露疑惑,秦嬷嬷解释,
“夫人嫁过来时,老爷还是礼部员外郎,俸禄微薄,养不起这偌大的宅院,是夫人从嫁妆里拨出一些,充做府中花用,还有老爷平日里人情往来,上下打点,都是从这里出的。后来夫人去世后,老爷也没有再提及此事,我一个奴仆更没有资格提,这笔账就一直糊涂下去。”
容钰眉梢微挑,眼里浮现一抹兴奋。
“堂堂礼部侍郎大人,竟然挪用已故妻子的嫁妆,说出去岂不是让人笑掉大牙。这可不行,我可不能让父亲被人耻笑!”
一行人收拾好东西,刚出了容府大门,气晕的容修永就醒过来了,还恨恨地念叨着,“我要和这逆子断绝关系!”
白氏眼珠转了转,捂住容修永的手,“老爷,三郎就是性子顽劣了些,您当父亲的,就当让着小辈了,更何况——”
白氏为难地开口,“这要是真断绝了关系,杨氏那些嫁妆……”
白氏一直都在打杨氏遗产的主意,前几年杨氏刚去世时,她就提过要替年幼的容钰把持嫁妆,理由冠冕堂皇,还暗示秦嬷嬷图谋不轨。
好在秦嬷嬷咬死不松手,容钰也没那么蠢,比起虚伪的白氏,他更相信从小服侍他长大的奶娘。
可这么多年来白氏从来没有死心过,要知道从杨氏嫁妆里拨出的那么一点,就足以养活偌大的容府,那完整的嫁妆该是多那么大的一笔财富,她光是想想都眼热。
这要是真断绝了关系,容钰带着杨氏的嫁妆一走,她可再没有机会了。
白氏欲言又止,容修永却瞬间明白她话里含义,瞪大眼睛道:“那是她的嫁妆,是留给容钰的,你怎么敢惦记!”
白氏愣了愣,神色委屈起来,“老爷这是怪我贪心了?我还不是为了这个家,光靠老爷的俸禄根本撑不起府中的吃穿用度,更何况老爷在外面还要应酬打点,哪些地方不要钱。别以为我不知道如今府中的进项都是从杨氏嫁妆里出的……”
看着容修永涨红的脸,白氏的声音也渐渐小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