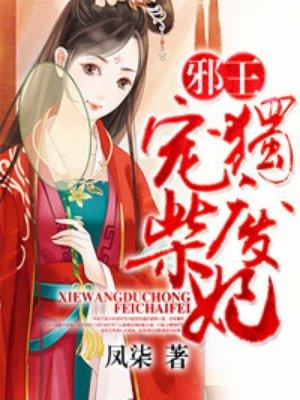第7小说>君为客 > 第413章(第1页)
第413章(第1页)
细雪,高杉,浓云天;
长剑,重刀,不屈人。
要如何才能赢?
那双凤目熬得通红,双手冻得皲裂,血干了再流,痂结了再撕开,他光是攥剑都像是贴着剥去表皮的粉肉。
狂风在吊着嗓子嘶吼,那二人却是沉默地挥刀动剑,几近干涸的气力在支撑着他们不叫肉|体与魂灵分割。
那伯策的一只臂膀中剑,这会儿伤口已流脓。宋诀陵却也没好到哪儿去,他的左手骨被伯策某回进攻时,徒手掰断,这会儿骨折处发肿得很是嚇人。
他二人却浑然不知痛,一味思虑着进攻。
宋诀陵聚目凝神,如同鹰隼般品鉴着猎物的呼吸,在那伯策转马避树的顷刻送剑上前。
“锵”一声,那剑被伯策背身拦截,转而便是转马时的一记刀背重挡。
伯策已至宋诀陵他爹那般年纪,蛮力却见长不见消,然那宋诀陵亦非等闲之辈,他力气不比伯策,耐力却很惊人,直叫伯策咬得齿碎,才终于将那宋诀陵的剑给弹开。
刺,捅,刮,砍,削。
宋诀陵的每一剑都有门道,逼得那伯策再来不及思索招式,像个初识刀剑者,执刀乱砍一气。
刀剑相撞,过于激荡的震意叫他们的双手疼得不自禁撒开。
宋诀陵忙忙转了紫章锦,要取弓射箭。伯策看穿他的意图,策马急追。
“魏家小儿,你打哪里去?!”重刀脱手,本是因十指脱力,这会儿那伯策却将十指攥成拳,汇满力量的拳点一下又一下地往宋诀陵的脏腑轰去。
在伯策近身冲宋诀陵挥拳时,他忽而瞥见了那对阴鸷凤目中的悚人笑意。
就是他挥拳上前的一霎间,那宋诀陵指间藏着的利刃一把割开了他的颈子。
他想起谁人曾言,宋诀陵能叫刀剑无声。
殷红长河自那伯策的颈子漫出,有如飞瀑似的猛流
他掉下马时,瞳子还随着宋诀陵迟缓地转,眼神那么悲哀,那么不甘。
伯策清楚他适才若眼疾手快夺了刀,颈裂的便该是宋诀陵,可他不知宋诀陵是个彻头彻尾的赌|徒,为了赢,他甘愿铤而走险,甘愿将心脏掏出来摆在赌盘之上。
伯策死前放声大笑,笑声震得整片林子都在晃荡。
伯策狠命瞪着眼,他淌泪说:“我老了。”
宋诀陵下马,拾剑挑他的皮肉,说:“你输了。”
是夜,杉林落雪无星子,野物的吠叫此起彼伏。
风仍旧穿林打叶,却再无先前那般摧耳欲聋。那伯策死前还很聒噪,此刻彻底断气了,倒叫这林间显得太过安静。
宋诀陵甫一松开抿紧的唇线,瘀血霍地自口中喷出,浇得白雪漫红。
他筋疲力竭,或许不久便要死在这荒山,心情却是不错。
他哆嗦着手,隔甲去抚那心脏前侧放着的一小块帕子,却不敢拿出来瞧,怕给血弄脏了。
他忽地想到了什么,张了张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