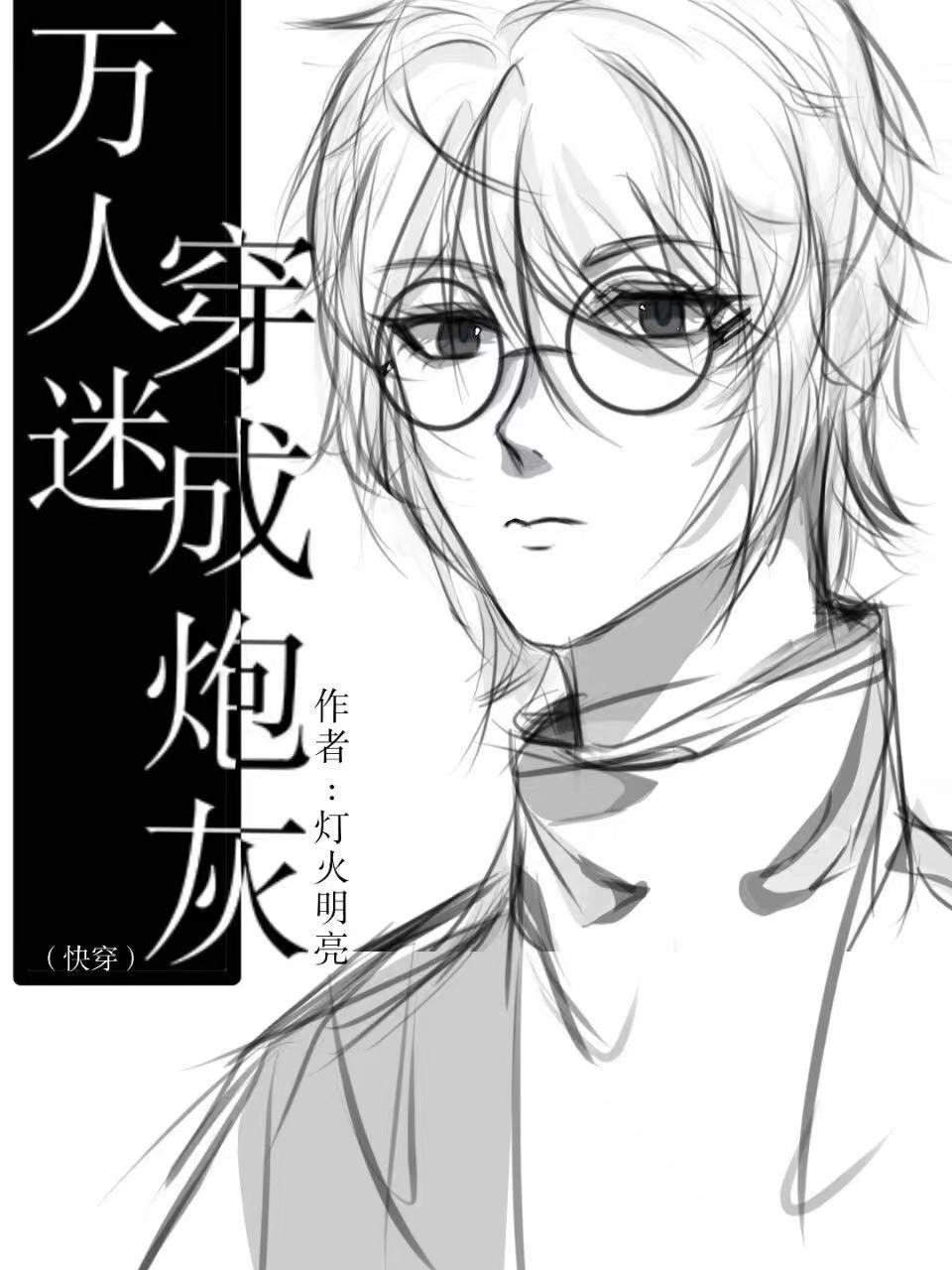第7小说>摄政王 > 第454章(第1页)
第454章(第1页)
小鹿大夫闭上眼,眼泪被长长的睫毛压得淌下来。
京营来人将携带半枚虎符,过永平府进入辽东,阻断金兵再次南下,并从陆上与複州相接应,等到城下,複州开城起义。宗政鸢一折研武堂驿报,用火折子燎了,京营的人便到了。
来的竟然是邬双樨和旭阳。
邬双樨和旭阳牵着马去见宗政鸢,半晌队伍后面才来军器局的马车。跟军器局接洽的是火器营教官队领队弗拉维尔,李在德一下马车,弗拉维尔敬礼:“您好。”
两个人对视,愣住。没想到对方是故人。那一回邬双樨和旭阳,主要是旭阳把弗拉维尔灌趴了,李在德去搜弗拉维尔身上的枪——那时还是夏天,热得蝉鸣声声,火烧的云霞像梦境——恍如隔世。
弗拉维尔笑了:“怎麽没看见那两位年轻英俊的将军。”
李在德笑:“他们在前面。”
弗拉维尔拿起一把改装鸟铳,拔下枪膛,看到膛线。李在德面红耳赤,以为弗拉维尔知道自己灌他。弗拉维尔倒是想,如果大晏能批量生産过硬的火器,能不能卖一些给葡萄牙。
“战事总会过去的。”弗拉维尔装上火铳。
军器局随行的除了火器工匠,还有小广东,弗拉维尔看到他倒是有几分亲近,因为他能说葡萄牙语。弗拉维尔跟小广东打招呼,想起小广东跑到教官营跳舞。教小广东跳舞的罗林已经不在了。
“总会太平的。”弗拉维尔自言自语。
武英殿散朝,皇帝陛下留下曾芝龙,叫出曾森。曾森扑进曾芝龙怀里,嚎啕大哭。数月不见,曾森北京口音愈发标準,哭起来都字正腔圆。曾芝龙半蹲下,搂住他。皇帝陛下离开武英殿,交代富太监:“曾卿和他父亲许久未见,就在武英殿叙话,其他人不得打扰。”
曾芝龙抱着曾森把他拎到偏殿暖阁花炕上:“又重了。长个了。”
曾森抿着小嘴,眼泪哗哗淌,不停地抽泣。
曾芝龙摩挲曾森小小的背:“你这几个月,还好吧。”
曾森一边收不住地哭一边急急忙忙道:“我种痘了,和皇帝陛下一样,以后就不怕天花了。”
曾芝龙一扬眉毛:“嗯?”
曾森一抽一抽地着急说话,曾芝龙拍着他。不想这个大胖儿子是不可能的,曾芝龙就这一个孩子。海盗的孩子注定是浮萍,海浪涌到哪里,浮萍水草飘到哪里。曾芝龙该舍也很舍得,不狠他活不到今天。曾森进京是当人质的,倒是没想到李家宽和,这小子混成个小王爷。
“不错,哪里都能混,是我的种。”
曾森一抽一抽的,感觉自己亲爹是在表扬自己,于是很高兴。
皇帝陛下很羡慕曾森,曾森的父亲还活着。他回到南司房,擡头问富太监:“大伴,先帝什麽样呀?”
皇帝陛下最近很惊恐地发现,自己好像在渐渐淡忘父亲的样子。不该这样,但是他就是留不住。
“看画像呀。先帝龙章凤姿,金声玉振,万中无一。”
皇帝陛下郁闷了,他不是要这些词。富太监心里一酸。陛下不敢去问太后,怕勾起太后伤心事。他低声道:“先帝还是皇子时,奴婢刚进宫。那麽多皇子,先帝站在那里,就像天人。”
“那我六叔呢?”
“先帝经常抱着殿下。”
皇帝陛下更郁闷,他不记得先帝抱过自己,为什麽六叔可以经常被先帝抱着?
“摄政王殿下现在不是经常抱您麽。”
皇帝陛下一听,好像也对。他珍藏着六叔给他的那封信。自己出生,先帝给六叔写信,喜极而泣。皇帝陛下心里一动:“先帝爱哭吗?”
富太监半天才回答:“先帝心软。”
远去的父亲忽然有了点温度。皇帝陛下开心起来,晃晃小脚,不再追问。
摄政王回到王府,鹿太医早等着。王都事解开李奉恕的外袍,头皮一麻。中衣全被血透了。
肩甲,背,腿,全都缝过针。李奉恕坐在武英殿就是熬下来的,他痛得全身发抖,但是没人能发现。鹿太医解开李奉恕身上血腥的裹帘,李奉恕白着嘴唇问王修:“士卒计数都完成了麽。”
王修麻利地帮主鹿太医,嘴上回答:“都完成了。金兵满蒙汉都有,根据尸体计数金兵中汉军损失最大,其中——”
鹿太医道:“我用特制的酒杀一杀,免得作脓,殿下你忍一忍。”
鹿太医小瓶子一倒,李奉恕抓着圆几闷哼一声。王修搂着他,示意鹿太医接着倒。李奉恕冷汗滚滚面如金纸,王修看着李奉恕痛得控制不住地痉挛,眼圈一红,眼睛往上看。
李奉恕埋在他怀里,含混地冒出一声:“疼……”
李奉恕睡得不安稳。王修怕碰到他身上的伤口,睡在外侧,撑着头看李奉恕。外间点着灯,一团渲开的熹微的光飘渺地笼着夜色,悠然宁静的一潭深水。李奉恕左肩下垫着东西,微微往里倾,大半个侧面浮出光影。王修仔仔细细端详他,看了这麽多年,怎麽都看不够。李奉恕长得兇,还是因为鼻梁太高,眼窝太深。看人的时候略略收下颌,眼睛微擡,剑眉往下一压,眼神看上去又暴戾又冷峻。王修从来没敢告诉李奉恕,当年他第一眼见着这位龙子风孙吓了一大跳,眼神太锋利了,剔骨刀一样。嘴唇薄,线条淩厉分明。李奉恕不是很爱笑,薄唇就尤其显得寡恩薄情。
其实不是的。王修微微凑近李奉恕,悄悄蹭蹭他。
李奉恕微微蠕动一下,王修起身拧个帕子轻轻蘸他脸上的冷汗。伤实在太多,鹿太医建议静养,李奉恕说现在不是静养的时候。白天在武英殿坐那麽久,伤口一直渗血,还不能给人发现。他从武英殿回来,王修有心理準备,看到血透中衣的惨烈还是受不了。李奉恕睡得不安稳,嘟囔一声。王修趴下去听,只有一个字,没听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