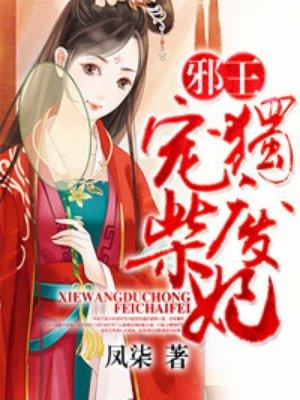第7小说>劣质占有 > 第225章(第1页)
第225章(第1页)
偶尔有小鸟驻留在阳台上,歪着脑袋好奇地打量藤椅上的男人。段从祯侧对着客厅这边,偏头的时候,即鹿看不清他脸上的神色。片刻,段从祯微微勾唇,眸中染上兴味,抬了手,夹着烟蒂,弹向落在栏杆上的鸟儿。羽毛擦过火光,小鸟惊恐鸣叫,翅膀扑簌簌地打在空中,跌落下去,好一会儿才缓缓飞起,迅速逃走。段从祯偏头支颐,好整以暇地望着抖落在阳台上的羽毛,深邃而危险的眼睛里染上愉悦笑意。即鹿就这样看着他,看他恶劣不堪,看他用烟头烫小鸟的羽毛,就像他曾经恐吓自己。扶在门框上的手缓缓收紧,没等即鹿转身回卧室,面前男人偏了头,散漫开口,“过来坐。”即鹿步伐一顿,微微叹了一口气,早已是睡意全无。走过去,四处看了看,没有多余的椅子,即鹿抿唇,正要回客厅拿一把,手腕被握住。段从祯拉着他的手,放下交叠的双腿,把人拉到腿上坐着。藤条椅本就凹陷,如此坐下去,即鹿便随着动作滑到他身上,两人靠在吊椅狭小的、半包围的环境里,气氛难免暧昧几分。段从祯抽手抱着他,从一旁拿过单薄毛毯递给他。即鹿伸手接下,披在手臂上,清晨的露水极重,染上几分凉爽。两人沉默地坐着,谁都没有说话,许久,还是即鹿开了口。“东青山的庭审时间出来了。”他说。段从祯懒散地垂睫,望着很远处的天际线,“嗯”了一声,没有多说话。“我要去看。”即鹿说。段从祯微微抬手,微冷的指尖抚过男人温热的后颈,眷恋似的摩挲,发丝擦过指腹,带出令人迷恋的温柔触觉。“去吧。”段从祯没多说什么。即鹿低眼,盯着地上的小药瓶,抬眼看他,“你为什么吃这个?”段从祯顺着他的目光看过去,漫不经心地说,“喜欢吃。”即鹿当然不信,“你能说真话吗?”“真话很没意思。”段从祯说。“吃药本身就不是有意思的事。”即鹿说,迟疑地看他,“你哪里疼?”目光试探着瞥向他右侧肩膀上的伤口。段从祯并没有回答他的问题,目光仍遥遥落在远处,鳞次栉比的建筑中,过了许久,才缓缓开口,却是答非所问,“我陪你去。”东青山的判决毫无例外,二审之后就已经盖棺定论,几个主犯都被判十年以上监禁,陪审团裁决的时间很短,几乎第一次就一致认为应判有罪,或许是真的为他们所作所为感到不齿,还要求重判。从法院走出来的时候,即鹿望着建筑缝隙里的太阳,心脏的跳动都慢下来。段从祯却似乎并没有他这样的轻松感。回去的路上,他一路都没有说话,即鹿悄悄看他,却看不透他在想什么。即鹿微微皱眉,心里莫名有些焦躁,呼吸变得沉重几分,忍不住打开车窗透气。“热?”段从祯注意到他的异常,偏了头看他。“有一点。”即鹿扯了扯领口,车窗缝隙吹进来的风将他头发吹乱。“去车顶吹风?”段从祯问,看了一下窗外,“太阳不是很大。”即鹿没答话,只摇头。他觉得很烦,很不安,很想骂人。明明最近一直担忧的事情得到了解决,东青山那群人也入了狱,可他还是很烦,他都不知道自己到底在焦躁什么。“怎么了?”段从祯望着他脸颊浮起病态绯红,微微皱眉,心想他是不是又惊恐发作,声音都带上担忧,“不舒服?”即鹿窝在座椅里,脸色不太好,却仍然摇摇头。段从祯盯着他看了一会儿,“还在担心东青山那群人?”即鹿没说话。“不用担心了。”段从祯抽手摸了摸他的脸,“他们的报应绝对不会止步于此。”即鹿微怔,有些惊愕地抬头看他,“你要干什么?”“我说过了,”段从祯淡笑,“他们会死在监狱里。”“……”即鹿呼吸重了许多,紧紧攥着拳,唇线抿直,许久,才缓声开口,“段从祯,这是犯法的,你知道吧?”段从祯到没有很意外,淡淡看了他一眼,“怎么?”“只是提醒你一下,”即鹿别过脸,脸色有点沉,也不太好看,嗓音生硬,“以防你不知道。”“啊,”段从祯懒洋洋应了一声,拖腔带调地开口,“我知道啊。”即鹿没说话,胸口略略起伏,像是轻哼了一声。“你不想他们死吗?”段从祯古怪地笑了笑,犹疑地看他,“还是说你同情他们?”“怎么可能!”即鹿冷声反驳,“没人比我更想他们死!可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