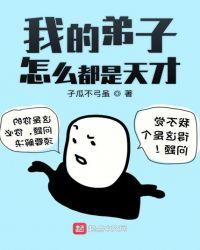第7小说>无名渡口 > 第112章(第1页)
第112章(第1页)
果然如杜若晴所说,如此恢弘的宫殿,四周却看不到一丝生气,相反,在深色天空的映衬下,这座沉寂而典雅的宫殿不可避免地笼罩上一层浓重的苍凉。
三人在厚重的大门前停了下来,这扇门的后面没有传出任何声响,宫殿的主人亦没有对他们这些久违的来客设置任何屏障。一个巨大的、专为他们而准备的陷阱即将就要铺向终点,他们想要的答案就在这扇神秘、庄严、古朴的大门之后——
星复伸手推开了这扇门。
满目琳琅,满眼猩红。
数十位衣着华贵的南平王室此刻如僵硬的木偶般以各种奇异的姿势躺在浓稠的血泊中,鲜艳的红色染遍了这座大殿的每个角落,四处充斥着浓郁的、刺鼻的鲜血的味道。长殿尽头,三四具尸体堆成一座小小的山丘,顶上的那人身披墨绿绸袍,银白的头顶豁然出现一道可怕的裂痕。尽管上一次见到这位老者是在二十余年前,杜若晴他们还是一眼就辨认出了南平王的背影。
“终于盼来你们了。”一道清亮的男声忽然自屏风后传来,一位高挑瘦削的少年从花纹繁复的屏风后走了出来,那少年一身黑衣,银白的长发自然而随意地束起,隐隐散发出幽紫的光芒。辞朔有些漫不经心地把玩着手中那把鲜血淋漓的镰刀,喂足了仙族的活血,这把纯黑的镰刀看起来更加美丽、光鲜,周身都散发着一股优雅而狠厉的气息。星复望着面前这片如注的尸山,暗暗咬紧了牙关,厉声道:
“你知道这样做,会带来什么后果吗?”
语罢,星复的手中已然多出了一道凌厉的剑锋。
辞朔忽然愣了一下,有些不知所措地来到南平王的尸体前,默默打量着他平静而衰老的面容,轻声道:
“当然知道,但,这些还远远不够。”
--------------------
说到这里,辞朔忽然抬起一只手,瘦到几乎只剩皮包骨的手臂上爬满了各种狰狞的伤疤,掌心凝聚起一股幽紫的灵气,宛若将独属于暗夜的一束鬼火带到了充满光鲜亮丽的尘世。它与这个世界格格不入,凡是见过它的所有人却又无法轻易忘却它的存在,优雅、美丽、魅惑人心,一点一点蚕食着妄图将它占为己有的狂徒们。
这抹美丽的荧光在他手中一点点散去,一同散去的还有辞朔脚下那些安静的躯体。他们的身体慢慢变成透明,纯白而晶莹的光点从他们的身体中飘了出去,在大殿的半空中不定地漂浮着,最后随着它们的□□一起消失。
“这这是,散魂术!”席鹭怔怔地望着头顶那片不断聚集,又不断散去的光幕,不可置信地喊道。
听闻魔界有三大秘术,集齐了这四海八荒最残忍、最奇诡、最神秘的三股力量。数千万年来,天界同魔界间总共经历了大大小小多达数千次的战争,双方的招式、战略也在千万年的迭代中轮换了无数次。尽管如此,却鲜少有人在战场上领略过魔界世代相传的那三种秘术,就算是那三种秘术究竟为哪些,多年来竟也鲜有人知。有人说,那三种秘术乃是这世间至诡、至残、至邪的术法,只有历任魔王才能够使用这股力量;有人说,使用这三种秘术的代价太高,它们中的每一个都违背了天道,凡是使用过这股力量的人最后都会遭到常人难以想象的反噬,堕入无极地狱。也许他们说的是对的,凡是使用过这股力量的人,性情都会变得异常凶残;同样,凡是见识过这股力量的人,最终都会被它折磨至死。
“噢,居然还有知道这个术法的人呐,”辞朔的一只眼睛不知何时已泛成灰白,纯黑的瞳孔浓缩成一条线,如密林中蟒蛇盯死猎物一般死死盯着席鹭的眼睛。他的嘴角勾起一抹笑,当他笑起来的时候,那双眼睛里明显地闪烁着某种兴奋的光,像是终于得到了想要的夸赞似的。
席鹭道:“不,我只听过它的名字。在此之前,我并不知道原来它就是你们魔界的三大秘术之一。”
杜若晴听了这话后,突然道:“这三种秘术,是魔界最高的机密之一。即便是魔族的一些长老,也不曾知道它们的名字。放眼整个魔界,唯一有资格学会并且使用它的,只有历任的魔王。但据我所知,史书上记载使用过这股力量的魔王,无一例外皆是在他们正值壮年之时暴毙身亡,这也是为什么,即便是在整个四海八荒最为开放、大胆,鱼龙混杂的魔界,也鲜少有人敢提及这三种秘术。”
头顶那片光点的力量变得越来越虚弱,平静的波涛下深藏着激烈而残忍的厮杀,终究会有那么一刻,就连这些神族后裔的魂魄,都无法升上他们想要去往的天国。
“更何况,他还动用了两种秘术。”星复望着辞朔无动于衷的脸庞,冷声道。
听罢,辞朔忽然发出了一阵大笑,毫无收敛、毫无愧疚的笑声回荡在古老空旷的南华殿中。南平王室的尸体已全然消散,他们再也没有了转世托生的机会,而那个酿就了他们所有的悲剧的魔族人,那名孤僻、阴沉、总是特立独行的混血少年,却站在他们心目中最为神圣、庄严、肃穆的神殿中恣意地嘲笑着他们心目中最为崇奉的信条。除了上次受伤后手臂上留下的伤疤,辞朔似乎并未因为此次屠戮遭受到丝毫的反噬,他的笑意是如此张扬,笑声是如此清亮,仿佛自信自己能够超脱这世间所有的因果,带着自己身上那股最引以为傲的邪恶走向世人极其渴望而终其一生却无法抵达的永生之境——
“对,对,我先是把他们都杀了,再把他们的魂魄都打散了,一般的人可没有我这样的修为和决心,把每件坏事都做得这么绝。”
“众生与众神于我而言,与这世间最为卑贱不堪的蝼蚁并没有什么区别。那些冠冕堂皇的仙君,在南平这么个破地方蜗居了这么多年,就因为他们的祖上与神族同源,所以他们可以世代受到上天庭的庇佑,这片注定被洪水和灾难吞噬的土地就可以生生不息地养育生命,他们本来就不该出现在这个世界上,他们不配!凭什么他们一出生就能理所应当地继承这里的一切,包括神族后裔的光环,与神族相当的力量、一呼百应的能力,恣意嘲笑乃至于打压所有不属于他们这个族群的人的权力?而我呢,我的父亲在人间是连中三元的旷世奇才,是当时的帝君亲口提拔上来的有名神君,而他在飞升之后做出的第一件事情,就是要把他那尚在襁褓之内的幼子赶尽杀绝。他这一生顺风顺水,不管做什么身边都簇拥着一大群人。他是整个天界公认最年轻的帝君,实力最强的审判神,怎么没见他对我跟对那些跟他非亲非故的贵族那么好啊?”
说到这里,辞朔眼底的笑意生长得更为疯狂,若是说起初他只是平静地承认了自己的残忍,到了他将话锋转向自己身上的时候,他的语气已经接近歇斯底里了。
“星复,你以为我愿意变成现在这样吗?我和母亲整日里东躲西藏,四处乞讨,城里那些攀炎附势的狗东西看不起我们母子俩,变着花样地羞辱我们、折磨我们,他是天神,是上天入地无所不能的武神,不可能不知道那时我和母亲已经落魄到什么地步了,尽管如此,他还是不折不挠地想要除掉我母亲,除掉我。我的母亲惨死在丰宇的手上,如果再不靠自己,我早就已经死了!这就是世态炎凉吗,这也太残忍了吧,怎么能这样对待一个当时什么都不懂的孩子?就算他是魔族的后代,应该也罪不至此吧?”
疯狂的呐喊宛若滔天的风浪般收不住脚,辞朔一手紧握浓黑诡异的镰刀,一边大步迈向殿门的星复三人,手中镰刀一挥,一阵银白的森风自南华殿外刮起,用力关上了他们身后唯一的出口。辞朔一边加快着手中的招式,那双迥异而恐怖的眼睛在星复身上来回巡梭,像是要在这个由内至外都接近完美的身躯上找到任何一点漏洞,那个他可以让他一击毙命的地方。辞朔望着星复没有丝毫表情的脸,忽然嘲讽地笑了起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