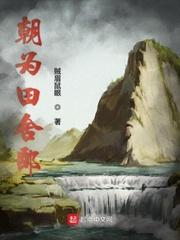第7小说>攻略殿下成功之后 > 第204章(第2页)
第204章(第2页)
真定大长公主面皮紫涨,用一种恨不得生啖其肉的目光狠狠地瞪着杨世醒。
她动了动身体,像要挣扎着从榻上起来。阮问颖见状不好,连忙上前扶住她的肩膀,假装给她整理衾被,实则偷偷使力按住她,避免其在一时冲动下做出什么过激之举,彻底惹恼杨世醒。
“祖母,你还好吗?可是觉得有点冷了?”
可惜她的这番苦心没有被大长公主领受,对方一边骂着她“孽障!离本宫远点!”,一边朝她挥手,还是杨世醒眼疾手快地拉过她,才没有让她被打。
她有些呆愣,没想到她的祖母会嫌恶她至此。杨世醒则是沉了脸,低喝道:“你做什么!”
真定大长公主喘着气冷笑:“本宫在做什么,你没有眼睛看吗?你方才不是说,若本宫胆敢对这孽障不好,就对本宫不敬么?好啊,本宫倒想看看你准备怎么对本宫不敬!”
杨世醒绷紧了下颔。
这是继七月别庄以来,阮问颖头一次见到他这么难看的神色,不由得心中一紧,伸手拉住他:“世醒哥哥——”
杨世醒就势把她拉到一旁,不让她靠近大长公主,也没让她继续把话说下去,冷眼瞧着躺在病榻上的人,道:“父皇已经知道了寒丹一事。”
大长公主脸上有恃无恐的神情消失了:“你说什么?!”
杨世醒没有理会,扬声唤三益入内,吩咐他把一样东西给大长公主服下。
三益俯首应是,从怀里掏出一个瓷瓶,倒出一枚药丸。
药丸的模样很像寒丹,瓷瓶的外表也很像曾经装有寒丹的瓷瓶,看得阮问颖惊疑不定,想要出声询问,但被杨世醒于暗中捏了捏手掌,就忍住了,没有开口。
大长公主又岂会认不出来?当下神色大变,破口大骂起来,从阮问颖骂到杨世醒,再骂到陛下和皇后,种种污言秽语不堪入耳。
阮问颖没想到她素来敬重的祖母会有这么一面,又是伤心又是可笑,彻底打消了替对方说话的念头,转过身捂住耳,低头闭眼,来了个不见不听不烦。
杨世醒要的就是这个结果,若不如此,她的心里永远会残存一丝不忍,被这丝不忍折磨、利用,只有彻底斩断,才能永绝后患。
见她做出了预想中的反应,他示意三益动作加快,后者遵从他的吩咐,十分利落地把药丸送入了榻上人的喉中。
怒骂声被挣扎声取代,接着,没过片刻,挣扎声没有了,一切动静都没有了。
阮问颖心里一抖,连忙转回身,看向榻上的真定大长公主。
“放心,她还活着。”杨世醒赶在她之前开口,“不过是让三益使了点小手段,让她暂时昏迷过去,免得她一直吵吵嚷嚷,听得我心烦。”
阮问颖松了口气,又觉得自己这个举动不好,仿佛不相信他似的,急忙向他解释:“我没有——”
“我知道。”他微微一笑。同样是打断话语,他这回做得就要比大长公主和方才的他自己温柔许多,一点也不使她觉得冒犯。“我能理解。”
他没有说他知道什么、能理解什么,但阮问颖清楚他的意思所指,也露出一个浅笑。
她回到他的身旁,垂了垂眸,询问他:“你……让三益给她服了什么药?”
寒丹性烈,给年轻女子服下都有性命之忧,何况老者?杨世醒是很厌恶大长公主,但绝不会真的动手,因为这样一来就会使她置于难地,而他不会让她陷入这种境况。
且他刚才说的那句话和让三益取出来的瓷瓶与药丸都太刻意了,刻意到她不得不多想的地步。
果然,身前人道:“能让她安静几天的药。你可以在这几天里清净一点,也有时间安排人手,避免她往后再无事生非。”
他说着,侧首看向三益,吩咐其把药交给外头的谷雨:“告诉她,以后若姑娘有吩咐,就把此药给大长公主服下,一丸即可。”
三益领命而退,不多时又提声禀报,道吴大夫过来了,是否要允其入内。
阮问颖一时犯了难,吴想容是她在之前让人去请的,一方面是为了给她祖母看病,另外一方面也是想让对方开点宁心安神的药,给大长公主服下。
这会儿可好,杨世醒先她一步把药给人服了,此刻正昏迷不醒。她是让吴想容进来,还是不让吴想容进来?
她看向杨世醒,无声朝对方征求意见。
杨世醒道:“让她进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