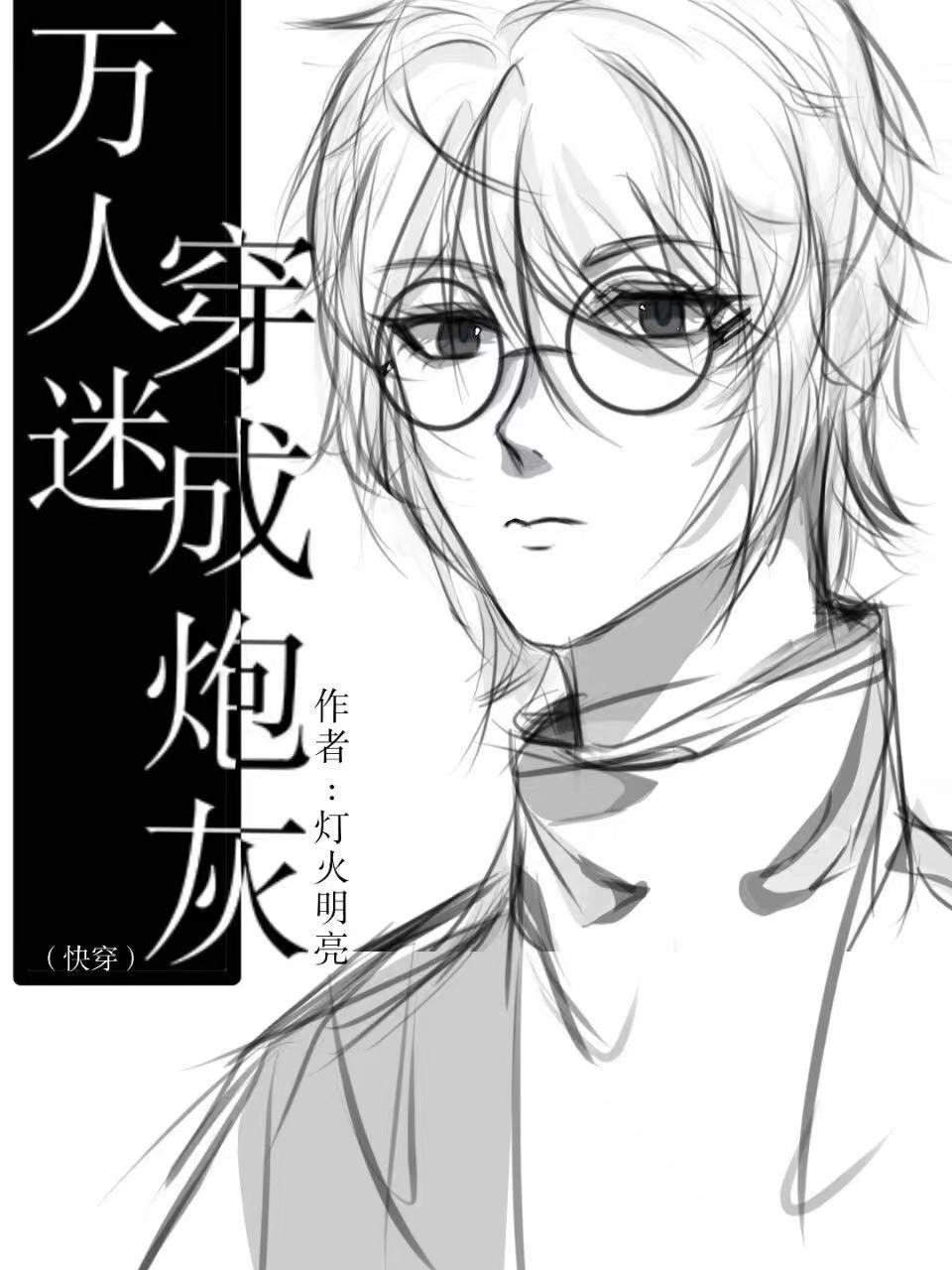第7小说>我从凡间来起点 > 第十四章 红袖添香夜读书(第2页)
第十四章 红袖添香夜读书(第2页)
这一夜过得格外漫长,直到晨曦微吐,张宝儿忽然起身,冲着在床上努力装睡的许易盈盈一礼,便小步出门去了。
待听到那道咿呀的关门声,许易才彻底放松下来,转瞬,便睡了过去。
这一觉直睡到傍晚,他才醒来,立时察觉到门外有人在来回焦急地走动着。
许易起身下床,挥开门道,“出了何事,张兄如此惊惶。”
张文凤赶进门道,“潘峰疯了,疯了,他竟请动了城隍府的通阴令,这回不但他的阴兵和游魂,要从咱们泗水地界走,还有其他三个阴将麾下的阴兵、游魂,也要从我泗水过境,他这是摆明了要报复。欺人太甚,欺人太甚,张某纵是泥人,也有几分土性。”
“这回我便是拼着这个河伯不当了,也要把姓潘的拉下马来。许兄,你与我有深恩,助我也已良多,张某不敢再求你出手相助。只是我这一去,生死未卜,是何结果,也说不准。唯一挂心的便是我家宝儿。只盼着许兄能看顾一二,许兄是至诚君子,一身修为惊世骇俗,唯有将宝儿托付给许兄,我才能心安。”
“还请许兄念在咱们的这段交情,千万答应。”
说着,张文凤竟拜倒下去。
许易挥手扫过一道气流,将张文凤扶起,“张兄言重了,不提咱们的缘分,单是张兄将重宝香火珠与我,我也自当为张兄过了这关,潘峰不是要聚阴兵,游魂过境么,我来料理就是了,必不让张兄失望。”,!
泗水水府的一干人等围满,张文凤三度举杯,为许易祝酒,许易饮罢,一干祝酒之人竟排起了长龙。
许易不愿扫了众人兴,酒到杯干,他终究不喜欢这等场合,见局面差不多了,便即告辞,返回他前番居住的雅间。
他推开门时,本就收拾一新的房间,又加了些点缀,红烛暖帐,芙蓉花开,分外温暖。
床前的香妃桌前,只着一件薄薄白衣的张宝儿,正灯下观书。
见得许易进门,张宝儿盈盈下拜,道,“公子救命之恩,妾无以为报,只恨妾蒲柳之姿,不能侍奉公子,只求公子能让妾在此间夜读,直到天明。”
她衣衫极薄,下拜之际,窈窕身姿,曲线毕露。
许易忍不住转过头去,为免荒魅胡言乱语,他干脆禁制了星空戒。
他返回时,张文凤也曾向他传出意念,希望他能和张宝儿同处一室,直到天明,毕竟,做戏做全套,要应付旁人眼目,谁也不能保证泗水水府中就没有别的眼睛。
许易本着帮忙帮到底的思想,念着左右都到这一步了,实在没必要矫情,便应承张文凤。
此刻,闻听张宝儿如是说,他再也不能赶人。
只是一见这张宝儿,他便忍不住气血涌动,偏偏他又要维系他假道学的名声,只好虚应了一句,径自上床,倒头便睡。
不知怎的,平素诵念几遍清心诀,再是烦乱的心绪都能平宁,只是今番不管他怎么用功,心绪都不得安宁,种种绮念,如走马灯一般,在脑海中盘旋。
好在张宝儿说到做到,除了偶尔添香,始终坐在桌前观书。
这一夜过得格外漫长,直到晨曦微吐,张宝儿忽然起身,冲着在床上努力装睡的许易盈盈一礼,便小步出门去了。
待听到那道咿呀的关门声,许易才彻底放松下来,转瞬,便睡了过去。
这一觉直睡到傍晚,他才醒来,立时察觉到门外有人在来回焦急地走动着。
许易起身下床,挥开门道,“出了何事,张兄如此惊惶。”
张文凤赶进门道,“潘峰疯了,疯了,他竟请动了城隍府的通阴令,这回不但他的阴兵和游魂,要从咱们泗水地界走,还有其他三个阴将麾下的阴兵、游魂,也要从我泗水过境,他这是摆明了要报复。欺人太甚,欺人太甚,张某纵是泥人,也有几分土性。”
“这回我便是拼着这个河伯不当了,也要把姓潘的拉下马来。许兄,你与我有深恩,助我也已良多,张某不敢再求你出手相助。只是我这一去,生死未卜,是何结果,也说不准。唯一挂心的便是我家宝儿。只盼着许兄能看顾一二,许兄是至诚君子,一身修为惊世骇俗,唯有将宝儿托付给许兄,我才能心安。”
“还请许兄念在咱们的这段交情,千万答应。”
说着,张文凤竟拜倒下去。
许易挥手扫过一道气流,将张文凤扶起,“张兄言重了,不提咱们的缘分,单是张兄将重宝香火珠与我,我也自当为张兄过了这关,潘峰不是要聚阴兵,游魂过境么,我来料理就是了,必不让张兄失望。”,!
泗水水府的一干人等围满,张文凤三度举杯,为许易祝酒,许易饮罢,一干祝酒之人竟排起了长龙。
许易不愿扫了众人兴,酒到杯干,他终究不喜欢这等场合,见局面差不多了,便即告辞,返回他前番居住的雅间。
他推开门时,本就收拾一新的房间,又加了些点缀,红烛暖帐,芙蓉花开,分外温暖。
床前的香妃桌前,只着一件薄薄白衣的张宝儿,正灯下观书。
见得许易进门,张宝儿盈盈下拜,道,“公子救命之恩,妾无以为报,只恨妾蒲柳之姿,不能侍奉公子,只求公子能让妾在此间夜读,直到天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