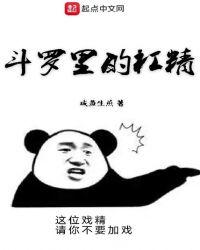第7小说>救命穿越兽世蛇夫超宠我下拉式漫画奇漫屋 > 第76章(第2页)
第76章(第2页)
他是真不懂他们殿下,但作为奴仆,他也没身份置喙。
祝知折是当真愉悦,就连语调都上扬了不少:“入套了么?”
十三知道他在说什么,低声回:“进圈了。”
祝知折颔首,又看了眼身后的营帐:“分批人暗中护着。”
十三低头说是。
而营帐内,因为踯躅不在,藕荷不会问仇夜雪要不要擦手烧衣服,所以仇夜雪是独自咬着牙平复了下心绪。
但他耳上的燥热才退一点,就又莫名想起祝知折在他手上和小腿上落下那两个吻的模样。
即便他没有看他,他也能够感觉到藏在那细长浓密的眼睫下的视线是带着多么浓郁的侵略性,直勾勾地,像是要将他吞没。
一想到这儿,仇夜雪就不住拧眉,说不出的烦躁袭上心头,让他想再往祝知折身上补一脚。
无论何事,他向来喜欢占据上风,亦喜欢掌控在自己手里。
可祝知折注定不是那个能被把控的性格,也屡屡出格越界……
仇夜雪狠狠捻了下自己的指骨,总觉得某人残留的温度还在上头,让他心里异样感更浓,几乎无法冷静。
烦死了。
谁能管管这神经病啊?!
次日一早,燕夏使臣便又闹了一通。
说是他们所带来的医官说万俟淞的手算是废了,日后不能提重物干重活,得亏伤得是左手,还能写写字。
但要上战场勒马拉弓,已是不可能的。
于是龛朝皇帝就安慰说那我们今儿就启程回京,让京中御医看看。
总觉得这里头环环相扣,还有什么算计的仇夜雪听罢后微挑了下眉。
上了马车后,仇夜雪就看着踯躅提溜着昨儿被她洗过澡的小狼崽上了马车。
仇夜雪看了眼:“不是让你送回太子那吗?”
踯躅:“奴婢去送了,但太子爷说这是送给世子你的,若是世子不要,那就丢回猎场等长大后被人宰了好了。”
仇夜雪总觉得祝知折这话是在威胁他,故而冷冷回了句:“那丢回去。”
刚好把小狼崽放在马车里的踯躅啊了声:“要丢回去啊?”
也不知道是不是昨儿被喂了一顿好的,今早又被踯躅投喂了新鲜的、不需要自己狩猎的肉,小狼崽在短短两餐里就乐不思蜀。
它又好似开了灵智一般,颠着腿跑到仇夜雪脚边撒娇打滚,还四脚朝天冲仇夜雪露出了肚皮求摸。
见仇夜雪看都不看它,它又主动用头蹭仇夜雪的脚。
在马车上,仇夜雪嫌靴子套着不舒服,故而是脱了靴,以一种极其闲散的姿势坐在软榻上。